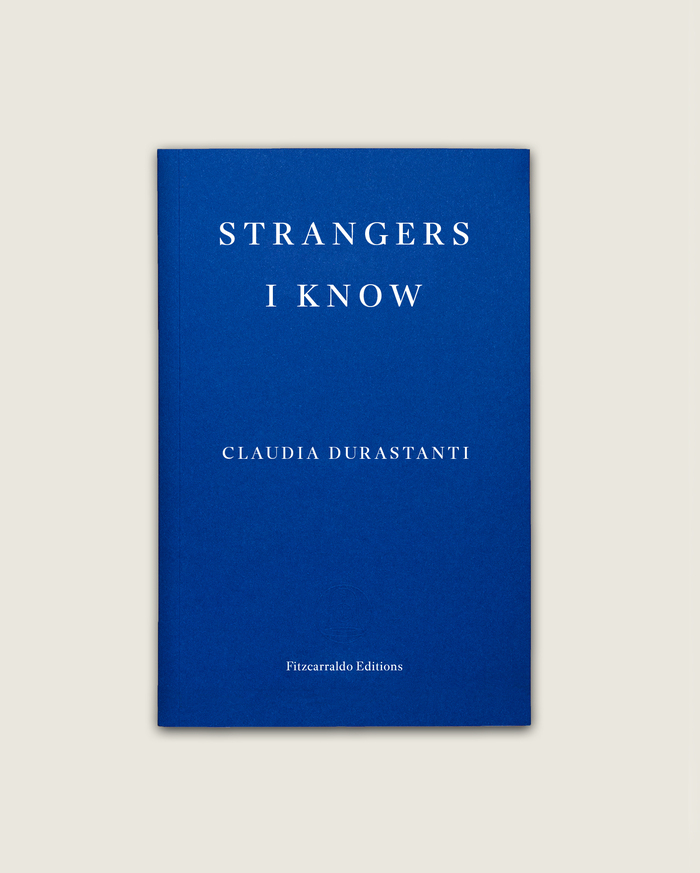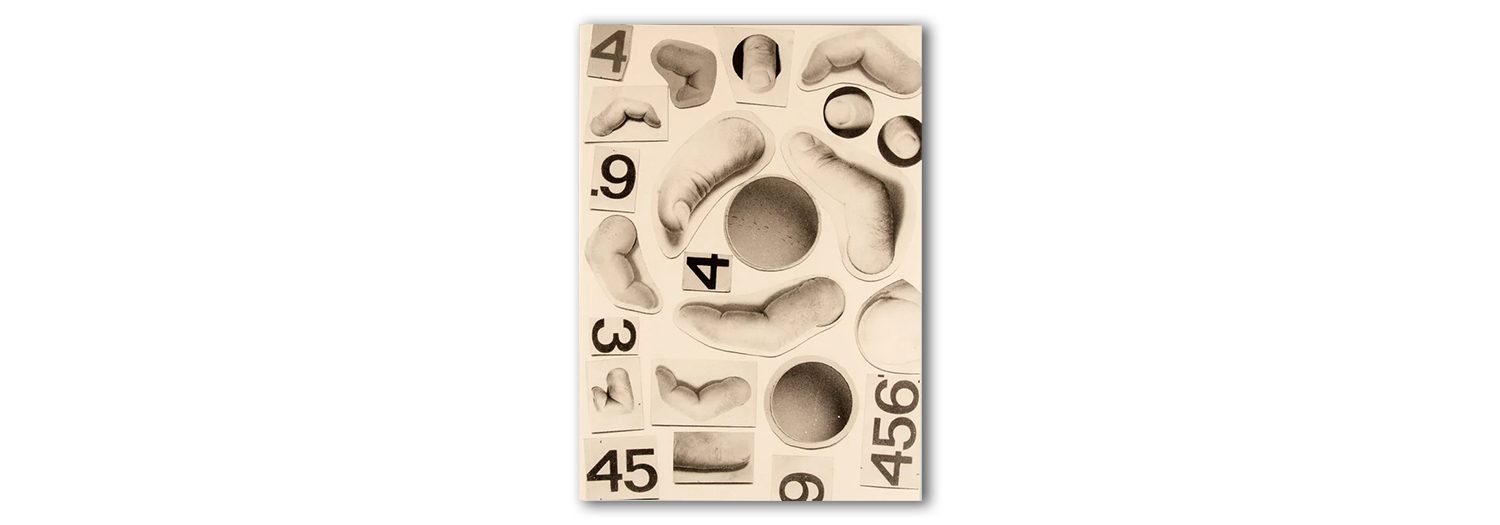在亚瑟·克拉克20世纪中期的科幻经典作品《童年的尽头》中,一个角色怀疑那些在遥远星球上经历巨大引力的居民是否意识到了第三维度。近年来,这一假设在我们不断增长的数字世界中找到了相似之处,在那里,我们不断被吸引到平板屏幕上,以确认自己的相关性,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
随着更多的信息被上传到以太网上,我们的存在会被我们在虚拟世界中遇到的东西所定义吗?科技行业似乎希望如此,从马克·扎克伯格可怕的反乌托邦metaverse计划开始。如果成功,实现我们的愿望将需要我们戴上耳机。metaverse和其他平台将通过鼓励我们操纵我们的个人资料并寻求验证来助长我们的成瘾。独立地发展一套丰富而连贯的价值观,将在数字环境中每天上演的令人担忧的政治和社会结局中失败。
对建筑师来说,这里有很多风险。我们的职责是设计有意义、富有参与感和刺激性的场所。理想情况下,我们创造它们是为了改善人类的体验,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并超越日常的现实成为崇高的东西。考虑到我们必须考虑的所有投入,这并不容易;成功需要一种有规律的方法,并得到研究的支持和对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认真倾听。感知和批判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视觉练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在空间意识中的作用要小得多。为了打破屏幕的视觉束缚,建筑物是否应该唤醒我们的其他感官?
正如阿米·西格尔的颠覆性电影《建筑师》中所表现的那样,许多建筑办公室已经变成了一排排电脑,设计师们静静地与屏幕互动,将虚拟现实呈现为三维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典型的里程碑是制作一个项目的附带效果图和视频,以描绘美丽的幻景。这些都是营销必需品,我的办公室和其他人一样使用它们,但几乎每次我看到一栋建筑或城市空间的照片后,都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当我接触它时,我的经验会逐渐减少,寻找使它以完美的预制形式提升的难以捉摸的魔力。
许多建筑师已经决定放弃承担责任,将设计工作交给那些知道如何将建筑组合在一起并愿意承担固有风险的办公室。这个过程的一个可能的未来和相当暗淡的迭代将使我们中的一些人决定一起跳过建筑,并将我们的建筑设计上传到云端体验。这不仅会强调哗众取宠而非能力,而且精心策划的虚拟空间体验将成为我们彼此完全远离的常态。
记忆影响着我们的感知,当我们体验到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时,我们的反应来自于我们的偏见、天生的好奇心和理解意愿。随着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些反应不断受到众包和嵌入式算法的影响,开始了缓慢而不可阻挡的取代直接体验的过程。当然,社交媒体也有好处。乔治·弗洛伊德、艾哈迈德·阿贝里和无数其他人被谋杀的视频,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关注点。但是,当涉及到在线人际互动时,我们在哪里划分文档和群体思维?我担心的是,对数字连接和肯定的迫切需求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的现实世界只会变成一个波将金村庄,成为虚拟世界的背景。未来几代人会意识到我们现实世界的丰富吗?或者他们会像扎克伯格的黑客帝国一样投入工作?
不管是好是坏,数字rubicon已经被超越了。很容易,完全有理由对堵塞地铁入口的人感到愤怒,疯狂地发出短信——这是对周围环境的无知。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孤立的表现,比如当我们看到一对夫妇坐在咖啡馆里盯着手机,或者我们被一个销售人员在更新他们的社交媒体信息时忽略了。如果建筑物成为用户的第二体验,因为他们渴望数字连接,那么建筑的意义何在?
建筑师在设计和做出选择时积极吸收影响,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设计技巧来增加公众参与。其结果,就像艺术一样,在他们所服务的社区的诠释中不断变化。人们应该想更多地了解他们走过的建筑和他们进入的公园。迎合亿万富翁们巨大的钱包和缺乏品味不会有任何帮助。我们的项目应该是柔软和令人愉快的,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同时唤醒休眠的感觉系统。就像华盛顿广场公园里那个在地上画社区圈的家伙,我们的设计能把游客聚集成社会联系的同心圆吗?也许有一些区域关闭了蜂窝信号,允许访问超本地化网络,这些网络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环境影响、设计成就、能源表现、公平倡议等。
通过有意地创造一些有限而真实的东西,建筑师可以培育出一个不断增长的意识图谱,照亮一个社区的灵魂。 建筑师在他们的实践中面临许多挑战:我们如何创造更多的负担得起的住房?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答案是难以捉摸的,但是当我们开始研究和设计我们不完全了解的东西时,我们不是更好的建筑师吗?我们的成功是由最终建成的东西来衡量的,我们必须面对数字世界对我们工作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可以拯救第三维度,不是通过设计更好的手机存储袋,而是通过认识到我们的角色是利用我们的技能在我们创造的物理世界中培养更好、更健康的社会联系。否则,如果我们遵循科技之神为我们铺设的道路,虚拟世界将会超越我们,并开始削弱我们作为新的、更好的现实的创造者、思想家和创新者的作用。